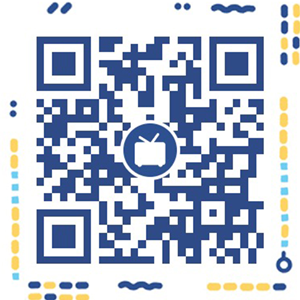傅聪访谈录
李玮彦
李玮彦(以下简称 李):一直以来,某些人对海顿的看法都是“不够有深度,不如莫扎特、贝多芬”,为什么海顿会给这么多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呢?
傅聪(以下简称 傅):因为一般人不会弹海顿,对他的理解不够,所以总是贫乏。事实上海顿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作曲家,对演奏家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他是一个初创者,所有的形式都是他奠定的,在他手里才形成了交响曲、四重奏还有奏鸣曲,所以他的作品里有从很多角度做许多不同的试验,不像贝多芬,贝多芬基本上是海顿的学生,很多东西都是从海顿那儿学来的,当然贝多芬到了他中后期形式已经发展得很自由了,但是基本上他的音乐语言是比较有规律的。但海顿不是,他的东西真是花样百出,要表现他的音乐需要很高的想象力,而且对音乐一定要很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海顿的分句都很微妙,相当错综复杂,一般人根本就不会去注意。另外他的弦乐四重奏是最重要的,他所有的音乐里都有弦乐四重奏,所以在弹海顿时,要听到很多声部,两只手独立的对话。除非你把它做到,不然就会平淡无奇。世界上很多人对海顿都很疏忽,听了我的海顿都大吃一惊,我有一个北京朋友说以前一直以为海顿就是一个“大家都认识的古人”,具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像从来没有注意过。
李:您刚刚提到想象力,我这次弹他的第13奏鸣曲,就发现通篇没有一个力度记号,可以有无限的可能。
傅:对啊!那个作品好极了!好的不得了!非常早期的,精彩极了!可是你要懂音乐!我们学生的好学精神还需提高,我在KOMOU的大师班,简直坐满了,那些学生从来不错过的,而他们是什么水平啊,是世界上最好的年轻钢琴家,那是什么样的音乐修养啊,最一流的!
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作为音乐学院的学生,大多都是经过多年的专业学习与练习的,但是,普遍的,对于奏鸣曲,不管是莫扎特也好,贝多芬也好,舒伯特也好,对于这些奏鸣曲的二乐章,总是无法准确的把握和演奏,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吗?
傅:因为二乐章一般都是慢乐章,是需要真正的音乐的!施纳贝尔就说他自己最擅长弹慢乐章。音符少嘛,音符和音符之间要表达的太多,需要很多的功夫的。
李:这次有个小男孩的音乐会,弹的奏鸣曲几乎都是第一乐章。
傅:我对这些所谓的神童是一点不敢领教的,口气都很大,将来都要做第二霍洛维兹,霍洛维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比他好的太多了,他不过是炫技,成功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真正懂音乐的人心中对音乐的评判标准和一般人是完全不同的。
李:您曾经说过,舒伯特的音乐最接近陶渊明诗歌的境界,可是陶渊明是一个很超脱的人,他可以辞官归田、“采菊东篱下”;而舒伯特终其一生都沉溺于才华得不到施展的极度痛苦与矛盾之中,是什么让您把这两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呢?
傅:舒伯特是个非常孤独的人,他的音乐是所有音乐家里最接近大自然的,比如说《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他好像是偶然从外星来的一个游子,我们都熟悉的《未完成交响曲》,一开始那种神秘,(唱)那种自然界,中间,很恐怖的,和贝多芬是两样的,贝多芬是个“我”字,可是舒伯特的音乐是超出个人的,他的音乐有种很神秘的,自然地力量。这一点和陶渊明很接近。看过很多陶渊明的诗吗?他有很多关于死亡的诗,托气吞山河,舒伯特对死亡的敏感和陶有很多相似。陶渊明在晋朝是出世的,舒伯特在他那个时代也是出世的虽然他的生活是整天和一大堆朋友唱歌啊,玩耍啊,可是他的内心还是很孤独的,不要去看表象。还有最后一个奏鸣曲(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没有比那个更接近的了,可是他的内心很孤独,那种音乐里的境界、心灵的境界是很高的。(对李)你这次弹哪一首?
李:舒伯特a小调奏鸣曲D.845。
傅:那个也是!多么神秘啊!(唱)那种问号,多么谦虚的问号!这个就跟陶渊明很像。可是到了高潮的时候,那种力量,不是个人的力量,是大自然的力量,是命运的力量。舒伯特的灵魂和一般的欧洲人不一样,他也基本上没有宗教信仰,他的宗教音乐基本上都不叫宗教音乐,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对自然的感受非常强烈,这个不是花和草,比这个神秘多了,是一种永恒的自然。一样是C小调,955.958,最后那个乐章就是死亡之舞啊! 整个宇宙的死亡,没有一点点怜悯,非常值得谦卑,可是又非常值得恐怖。那是对大自然的恐怖,为什么一直以来就有图腾崇拜啊,然后又是宗教,就是因为人对自然的……
李、谈佳韵(以下简称 谈):敬畏。
傅:对。我们现代人被现代化的“方便”遮盖了很多,对自然都已经没有感觉了,而且不够敏感,不光对音乐,对生活,对生命本身都不够敏感。可是我还是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看你的灵魂有没有,你的灵魂里有,就能感觉到,无时不在。还有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宗教情绪,这和具体的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信任何教,可是我的宗教情绪非常强烈。那是一种比渺小的个人更神奇的和整个宇宙的通感,每个星期去做礼拜的人,很多都只是一种形式。
李:人们往往觉得悲剧性的音乐更能触及内心,更有人说艺术家本身就是悲剧性的,这个所谓的“悲剧性”真的存在于艺术家身上吗?
傅:这个悲剧性可能有点严重了,这里要用这个词,vulnerable,就是很容易被伤害,因为他真,他是透明的,你说他很脆弱,他确实很脆弱,可是他又很强,他没有被世俗的东西所侵蚀,应该是这样!有几个人真正称得上是艺术家?有很多人都是“用”艺术,并不是为艺术服务,是炫耀自己,为自己涂脂抹粉。
谈:对于您来说开音乐是没有什么压力咯?
傅:压力嘛总归是有的呀。
谈:您追求完美。
傅:生命是不可能完美的。所谓完美,只有一样东西是完美的,那就是死亡,活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完美,它永远在生长,只有死掉的东西才是完美的。我对音乐的追求也永远是一个过程,给学生上课也就是一个追求的过程。我讲课和别人不一样,我不是仅仅把我知道的告诉学生,而是和学生一起去发掘,所以同一个曲子,我每一次讲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每一次都重新发现。
李:您的压力是来自于音乐本身。
傅:对!
谈:对于我们来说,通常会有“当局者迷”的这样一个现象,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傅:是这样,会有的。中国美学里有一句话叫“能入能出”,这种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第一步就是“入”,不“入”是无所谓“出”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有几句名言说的太好了——“凡大艺术家,必经三阶段,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
傅、李:为伊消得人憔悴。
傅:最后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错不错!都知道这些诗,很不错!(笑)
傅:可是你说他是在说什么?你替我解释一下
李: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他独自一人……
傅:第一句也是很重要的哟!昨夜西风凋碧树,这就是我说的最原始的宗教感,就是舒伯特对自然地感受。然后非常重要的,“独”,独上“高”楼,“望”,望尽天涯路,这个人就是胸中有丘壑了,对不对?“独上”,这个“独”和贝多芬不一样,是舒伯特的那种独。这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可是他是通神的。他看得很远很远,而且他追求。这就是第一境界,你心里有这种感受就会“入”。第二个境界就是忘我的追求。第三个境界,“众里寻他”,寻不着,“蓦然回首”,悟了!他(王国维)说没有哪个境界是可以跳过的。到那个境界就入了也出了。我太欣赏他了,太伟大了,而且他用这么美的诗来说,讲理论可以讲得如此的感人。做艺术就是这样,把自己完全投入进去,可同时还要有客观的控制,如果在里面迷了、狂了,就不好了。有的人就是一辈子都出不来。
李:好多人一辈子连进都进不了。
傅:对啊!
李:艺术来源于生活,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后才写出不朽的作品的,可是作为学生,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太多太多,于是经常都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没有经历过,怎么会懂啊?”您觉得这能站得住脚吗?
傅:这个很难说。我12岁的时候偷偷看了李后主的词,感动得不得了,那时候的我经历过什么啊?可是我能感受到!每个人的天性不一样。当然,像我小时侯,逃过难啊什么的,这些也感受过,可是如果真的对音乐有感觉就能够体会得到。
谈:能谈谈您眼中的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吗?
傅:海顿是非常健康的,我就是要说这一点。健康而能感人就更加不简单,海顿是所有作曲家中最富有幽默感的,而且是个农民,他有那种农民的朴素和天真,泥土气息、生活气息很浓。他很爱生活,对生活的热爱在他的作品中无处不在,整个音乐活的不得了、新鲜得不得了。而且他的慢乐章绝不缺乏深刻,贝多芬慢乐章那种悲剧性在一定程度上海顿也有,可是对于海顿,说“悲剧性”就太言重了点。海顿那个时代,18世纪,在欧洲,他们叫百科全书,比如福尔德,他们那个时候对中国的哲学很感兴趣,从孔子、孟子、庄子中吸取了很多养料。他们认为东方人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平衡,什么是真正的中庸之道。相对的说,从历史眼光来看,那时候贵族和贫民的矛盾还没有到要爆发革命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维持了平衡,比如说海顿在埃斯特哈奇公爵门下做他的家庭音乐家,替他整天作曲,基本就等于是
前几天刚听说我有疑问,
在这里,要特别感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