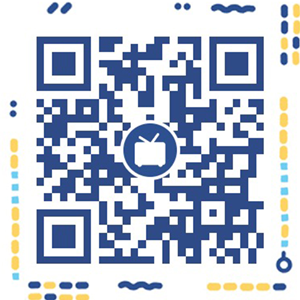七月,骄阳似火。一幢法国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小楼,一间典雅古朴的会议室,一张陈旧的会议桌,一杯浓郁回味的咖啡,一群为文化教育孜孜耕耘的园丁,以茶话会的形式鸣谢在我院教学八年的外聘教师——作家展望之副教授,这也是公共基础部历史上首次为一位外聘教师举行这样的聚会。
展望之老师2000年退休于上师大教科院,同年9月受大学同学、时任我部语文教研室主任、身患重病的彭皓权老师之托前来代课。之后不久,彭老师病故,展老师在非常时期撑起了上音语文教学的一片天。八年中,展老师以望七之身先后开设了《大学语文》、《文学概论》、《古汉语》、《名篇选读》、《外国文学》、《美学》、《红楼梦赏鉴》等课程。同时,广泛参与和指导我院校园文化建设,为提升我院学生的人文综合素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难能可贵的是,展老师超越了一般外聘教师常有的由身份所导致的意识、心态和作为上的局限,他把对朋友的承诺、对音乐的崇敬、对学生的挚爱和对教育的热忱转化为上音课堂上的精彩讲解,其锦口绣语及俨、温、厉的师范获得了我院众多师生的好评和爱戴。
茶话会上,许多教师以自己的亲历发表了对展老师的感佩,公共基础部主任奚爱茗副教授用 “信、达、雅”三字赞誉了展老师的为人、博学和襟怀风神,并代表公共基础部全体教师以一尊寓意深刻的青铜“大克鼎” (交大仿制)相赠,以示敬谢。展望之老师颇为感慨地叙述了他与上音的因缘,最后以一首七律诗表达了对上音八年的留恋和自己从上音“退休”后将“闭紧嘴巴,放开手脚”、多走多写的晚年安排。
附:展望之先生有关上音的诗文
跌进殿堂
我考过上海戏剧学院,专业没问题,从初试到复试,当时的先后主考田稼和朱端钧两位先生都很赏识我,与我亲切地交谈,时间远远超过其他考生。最后让我去一小房间,里面有一位老师坐等在钢琴边。叫我唱一支歌,我说不会。随便什么歌都可以,我摇摇头,那就唱《社会主义好》吧,我几乎要哭出来了,还是不会。老师的表情显得很惊讶,还带点愤怒,挥了挥手,那就去吧。我出了房间就知道:完了。那时搞文艺的人,称谓文艺战士。不会唱《社会主义好》,就是战士没有武器,没有武器,又如何打击敌人,团结人民大众?我清楚我的名字已经排在孙山后面了。
我真的一首歌也不会唱,尽管我的嗓子很好。说来奇怪,我又是一个非常喜欢听音乐的人,尤其是西方音乐,从巴赫、亨德尔到德彪西,我都熟悉,爱听,最喜爱的曲子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和舒曼的《梦幻曲》,我对音乐的陶醉,一点也不亚如我对文学的痴迷。不过,说来有点难为情,再喜欢再熟悉的曲子,不管听多少遍,我还是一句旋律也哼不出。我是个音盲。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坐在音乐殿堂门槛上的人,挨得非常近,却又永远进不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一下子,跌了进去。我的一位大学的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在欧宝官方入口教文学,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他病了,让我去代他。我教了两年,他悄然而去了。在他的追悼会上我悲痛地说过:“你委托我,代替你上课,请放心,我会上好它的,我要将每一堂课,每一句话,都化作对你的深深的怀念。”我就在上音教文学了。在好几年之前,我曾经随意地对我这位同学谈起过,想到音乐学院来教书,后来虽然没有什么具体行动,但动过念,说过话,这就是佛家说的:因果,缘。
我的耳朵从此有福了,在这里,每天都可以听到音乐。我走到六楼,这间教室的门里传出萧邦的夜曲;来到七楼,那间教室里有舒伯特的曲子,八楼,不知哪儿响起了《二泉映月》……我常常抱着书拿着茶杯在课前课后伫足聆听。走在楼梯上,突然遇见茶花女或是卡门,唱着咏叹调从上面快步跑下。学期终了时,我会悄悄地走进一个小音乐厅,坐在后排,观赏声乐系、钢琴系或是管弦系考试,等于听了一场场小型的音乐会。贺渌汀音乐厅建成了,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精彩的音乐会,学生都会送票子给我,后来有的学生率性对我说,老师你喜欢听音乐就来好了,不用票子,我是在门口收票的。
我几乎每天在欧宝官方入口走进走出,而当我在念中学的时候,这里是很神圣的,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擅自走了进去,刚走到几株桂花树前,就被门卫喝住,赶了出去。所以,现在每当我走到桂花树前的时候总要看上它一眼。
音乐学院在汾阳路上,一到秋冬,路上铺满了黄色的落叶,踏上去会吱吱发响,我喜欢在这样的情景中去学校。一天,在校门口,大铁门旁边,有一个烘山芋炉子,卖山芋的汉子,戴着一副耳机,闭着双眼在聆听音乐,那种陶醉沉湎的样子,实在令人感动,这,只有在音乐学院门前才能够看得到。
我进了音乐殿堂,不是走进去的,是跌进去的。(原刊于《新民晚报》)
七律.别上音
八年似水去悠悠,
即到临行触目愁。
无绪时时弄白笔,
有缘处处说红楼。
管弦音绝已成梦,
花草香残犹是秋。
从此天涯留我影,
清风拂面月当头。